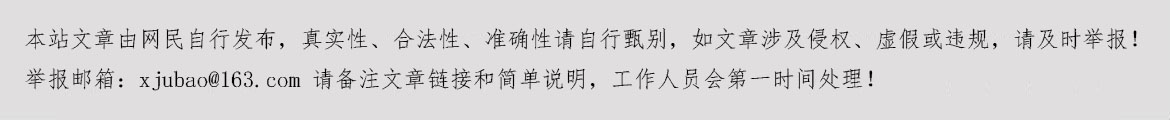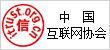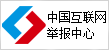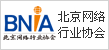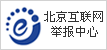除了大象,貉、蝙蝠、松鼠都进城了,我们该怎么办?
2021-06-06 23:44:33
新华社上海6月5日消息,一群亚洲象一路北上进入昆明市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闯入村庄、貉在上海100多个小区现身……
近期,多地不时出现野生动物进入人类栖息地的事件。对此,我们该怎么办?记者走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探索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王放教授团队,一起寻找答案。
城里来了不少“动物居民”
在上海,一场关于“动物居民”的调查正在进行。12个调查区域、300个红外相机专门为野生动物而设,在上海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王放团队希望通过一两年的跟踪观察,得到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示范方案。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不只是保护那么简单。”王放研究发现,部分野生物种在城市的数量快速增加,分布范围也在扩大。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为例,2015年,上海在40余个小区发现了貉的身影,到2020年,上海有貉的小区数量达到150余个,增长超过2倍。
↑上海某小区里拍到的貉。(王放提供)
“动物居民”增多后,人与动物的接触和冲突相应增多。研究表明,每公顷的貉在2只以下时,人们几乎不会感受到貉的存在,但当这一数字超过5只时,就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据团队统计,2020年,上海12315关于野生动物扰民的投诉达千条左右,其中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噪声困扰,也有人被貉惊吓。除了貉,市民还对蝙蝠的存在感到不安,2021年又出现了针对赤腹松鼠毁坏花园等情形的投诉。
与此同时,貉的习性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独居到群体活动,从昼伏夜出到昼夜都活动,从怕人到主动接近人。“最大的改变是它们对人和人类世界的态度。”王放说,“过去隔着三四米远看到人马上就跑,但如果出现主动投喂等行为,它们会主动追着人要食物,这就有可能惊扰到老人和儿童。”
↑貉在城市小花园里。(王放提供)
貉在上海的变化,与野生动物在全球其他城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王放举例说:“比如欧洲的赤狐、美国的美洲黑熊和浣熊,都呈现出了快速城市化的特点,貉的变化方向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但变化速度之快让我们吃惊。”
它们为什么会“离家进城”?
野生动物为什么要离开原本生存的环境进入城市?王放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迁移是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没人能把野生动物限制在保护区里,动物迁移目的包括但不限于食物、水源、配偶、躲避天敌、寻找更好的栖息地。
“然而大家容易忽视的是,当栖息地变得破碎之后,很多动物失去了迁移的机会和迁移的能力,再次恢复迁移行为往往需要几十年去探索重建。包括亚洲象在内,很多物种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它们会试错、会冲突、会跑到看起来‘不该去’的地方,但是这些过程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王放说。
其次,相比于荒野和城乡接合部,城市环境的恢复速度更快。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高达40%,不仅有大面积的森林和湿地,还有街心花园、口袋公园等小而美的生态区域。这时候,城市会像一个热点,把周边的动物吸引过来。
最后,城市的环境给一些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貉、松鼠、黄鼠狼等动物的生活方式非常灵活,它们善于根据城市的特点调整,城市里没有天敌,只要能适应城市生活和人类,他们就几乎不会遇到威胁。
↑两只貉在城市里。(王放提供)
如何在冲撞中共存?
野生动物“进城”,城市居民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好奇,到不满,再到各退一点逐渐习惯,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会形成新的秩序。
王放认为,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对野生动物的了解和对城市管理的研究。在过去一年里,王放团队在上海开展广泛研究,基本掌握了貉在城市里的变化,除确定每公顷数量阈值外,还建立栖息地模型进一步分析驱动野生动物发生变化的机制。
“我们发现,貉不需要大片的森林和绿地,影响它们分布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灌木丛和水源。它们还喜欢中小型的公路,白天公路上车来车往,夜里就成了动物们的‘高速通道’。”赵倩倩是王放团队的一员,她前前后后共为5只貉戴上有定位等功能的颈圈。
↑志愿者一起讨论城市野生动物调查。(王放提供)
在不妨碍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之下,城市野生动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截至目前,各地政府和市民都对野生动物“进城”保持着很大程度的容忍,不仅帮助闯入村庄的东北虎回归山野,还承受了大象“观光”造成的数百万元经济损失。
但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干预举措。据王放介绍,2020年7月,上海市一个小区的数十只貉群体性行为失常,造成很大干扰。为此,上海市开出了第一张野生动物狩猎证,将小区内的貉捕捉后安全转移到了野外环境。
王放还表示,解决野生动物“进城”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做好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保留城市缓冲带,尽量减少野生动物与城市居民的直接冲突。
“城市首先是人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野生动物管理永远没有最优方案,冲突会一直存在。不管多好的制度,都需要持续调整。在这方面,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大量探索,经验异常珍贵。”王放说。
来源:新华网
相关报道:
15头野象进昆明4天专家:再走下去可能会有小象累死
来自西双版纳的“断鼻家族”已经在昆明境内活动四天了。
6月2日21时55分,北迁的15头野象正式踏入昆明地界,进入晋宁区双河乡。截至6月4日17时,象群向西南迁移了6.6公里,持续在双河乡活动。
6月4日16时许,全现在在昆明安宁市与晋宁区交界处看到一排渣土车停靠在路边,以及6辆满载香蕉、玉米、菠萝等用来投喂大象食物的车,其中还有200斤酒糟。
一位渣土车司机告诉全现在,他们是安宁的车队,从3日一早接到通知称大象可能进入安宁地界,便来此处围堵象群。此次总共出动了13台车,每辆车约3米高,净重十五六吨,“大象过来,我们就开车过去把路堵起来,让大象往山上走。过了这里,大象就进入安宁地界了。”该处距离大象当时所在的晋宁区法古甸村不到三公里。
用来拦阻大象的渣土车。
但一直到6月4日晚上,大象都没有经过上述地点。据我们视频,6月5日凌晨一点多,象群正在慢悠悠经过晋宁区绿溪新村的农田。
至此,这15头野象已经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14个月,向北迁徙了400多公里,距离昆明主城区约60公里。象群为何还在继续向北行进,此前采取的围堵、诱导等办法是否难以奏效,事件未来的可能走向是什么,以及有哪些减少人象冲突的案例可以借鉴等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全现在就以上问题采访了数位研究大象多年的专家。
“是因为慌了,不是为了找吃的”
全现在:目前一直在采取围堵和诱导等方式试图影响大象行进路线,为什么象群还在一路北上?
吴兆录(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教授):大象为什么一路向北,按照从生物学、生态学来解释,现在说不清楚。有人认为它们是来寻找栖息地,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原有的栖息地遭到了一定程度破坏。但它们越往北走,经过和到达的地方并不那么适合它们生活,所以说它是主动出去,往北寻找好的栖息地这种说法,有点牵强。
要注意,野象在西双版纳迁徙时,一般都会在地势较低的沟谷里行进,但象群到了(玉溪)峨山后,一直到(玉溪)红塔区,到昆明,它都是往山上走,因为沟谷里交通网络发达,人也多,它们害怕。但山林里并没有多少东西可吃,到了晚上,它们又下到平缓的地方,到村寨里、农田里寻找食物。
所以我认为,象群到了峨山之后的这些行为,不是主动行为,是逃避。它们就是害怕这里,在陌生的地方,旁边还有很多人为干扰。现在在昆明,用了14架无人机在后面跟着监测大象,我认为这已经非常过度了。我不是说方法错了,而是说现在大象为什么往往北走,是因为慌了,不是为了找吃的。
别人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是学术争鸣,至于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往北边走,只能去问大象。
2021年6月3日下午,象群在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活动。图片:CFP
孙全辉(环保组织“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大象已经走出保护区很久了,这样的现象是比较罕见的,针对这种情况,可能我们也没有太多经验。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不像被驯化的动物会听从人的指令,我们只能在保证人跟动物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引导它们,减少人象冲突。
目前能想到的办法我相信都用上了,比如说堵和疏导,用食物去诱导,可能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至于未来象群要到哪里才停下来,要怎么办,这个还需要去多方协商和研究。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证人员和动物的安全。当然从更长远的大象保护问题来看,还是要从栖息地着手,看看现在栖息地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否则即便我们真的把大象弄回去了,谁能保证它们不再出来呢?
全现在:要劝返或者引导大象回去为什么这么难?等着它们自然返回去的可能性大吗?
孙全辉:一是大象离开原来的栖息地太远了,有将近500公里,这中间,它们往哪个方向走存在很多偶然性。另外,一旦离开了熟悉的环境,我想整个象群也是处于一种惊慌的应激状态,有点慌不择路,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受到一些食物水源的吸引,就朝那边去了。某些时候因为路被堵住了,它们只能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这导致它形成了现在这样看起来并没有明显规律路线,如果沿线返回是比较困难的,可能还要经历很多这样的障碍。所以原路返回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投喂大象的玉米、香蕉、菠萝,以及酒糟。
现在等着象群自行返回的可能性也不大。首先要有满足它们生存所需的环境和条件,让它觉得比较安全,或者食物资源足够,但显然象群一路下来,如果不是人们投食,很可能它们的食物是不够的,它们有可能不会按照原来的路线回去。如果要再设计一条象群能够回去的通道,有没有这样的线路?能不能实现?就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
黄泓翔(非洲野生动物保护者、“中南屋”创始人):无论是在非洲还是亚洲,大象都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涉及到迁徙时,要么是因为它基因里面有的迁徙习惯影响,要么是在头象的带领下进行迁徙。大象是有自己想法的一种生物,人类要去引导它们本身就不会容易。如果引导大象真的是一件容易的事,世界各地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象冲突了。
要去引导大象的行为,常见措施无非就是堵截加诱导,我相信当地应该采取的措施都已经用了,这些措施采取之后是否不太有效?或者是否有某些因素导致并没有产生太大效果,不在现场的人很难加以评论。
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很难,在非洲也一样无解。比如在肯尼亚,大象会经常在国家公园附近迁徙,后来修了一条铁路来阻隔大象迁徙到接近人类的地方,并且修建了一些动物通道让大象通过。但实际上,还是会出现大象去闯铁路的现象,而没有按照人的引导去行动,所以要引导大象按照人类的想法去行动,本身就很难。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
全现在:如果天冷了,大象发现北边不适合生存,会不会往南走?
孙全辉:非洲象有这种长途迁徙跋涉习性,它们会随着季节的不同和食物资源的分布,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已经形成了它们生物学上的一种固定行为。但对于亚洲象来说,目前并没有发现它们有这样的习性,如果资源比较丰富,它们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游荡,而不会是像这次这样出走这么远的距离,来到一个完全没来过、也不太适合生存的环境。
当然,如果把时间尺度放长,从历史上来看,云南很多地方都是有大象分布的,甚至在中原地区都曾有大象的分布,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这些地方已经都没有亚洲象了。如果它们再回去,这些远古的栖息地早已经改变了,很多地方已经被开发成城镇、城市,或者农田,早已不再适合它们生存,还会引发很多人象冲突。
“最悲观的,可能会有小象累死”
全现在:事情接下来的走向可能是怎样的?如果大象继续北上,对人和对象来说,最悲观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吴兆录:象群里有三头非常小的幼象,一直这么跋山涉水跑来跑去,最悲观的,可能会有小象累死。我看到前一阵有视频显示小象掉进了沟里,万一有些象从悬崖上掉下去怎么办?实际上在西双版纳曾经发生过大象从山上摔下去死亡的意外,更何况现在有十几头大象,这样的危险也是存在的。
至于对人,现在看来没有多少威胁,因为相关部门一直在跟踪监测象群,预警做得很好。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伤人的事件,不是因为大象变得友善、温顺,而是因为这样的工作,避免了很多人象冲突。
所以说,事情继续发展下去,最危险的是大象,而不是人。
持续北上的“断鼻家族”。图片:CFP
孙全辉:顺着大象现在这样一个扩散路线,无论是气候、食物还是气候环境,现在的条件看起来都不适宜大象长期生活,最终可能还是会动用一些人工干预的手段,为它们寻找到一个妥善的地方安置。
但首先肯定不是动物园,因为这些野生动物也不适合关在动物园里,它们的生态价值要在自然界体现。其次,可能也不会一直放任,目前也动员了各种各样的力量,24小时的监测和不间断的预警,封锁大象沿途经过的地方。至于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措施,我相信现场的专家们正在思考解决方案。
因为有小象在,象群的警戒性或防御性会更强。出于天性,母象会本能要保护小象,在这种应激的状态下,如果过度惊扰它们,或者是抓捕造成一些紧张,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无论是对动物还是人都很危险。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大象不像一些小型动物,麻醉起来运输很方便。大象一旦被麻醉了,倒下去,内脏的压迫就可能会导致新的问题,甚至死亡,所以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的
又因为是十几头象在一起,怎么去操作,需要从动物、安全、技术等方面考虑,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应该不会很快有一个解决方法。
全现在:有专家预测,象群如果不向南返回,小种群可能存在灭绝的风险,这是可能的吗?为什么?
孙全辉:有可能。大象是以家族群活动的,象群中的成员都有亲缘关系。母象一般不会和同种群中的公象交配,这样也会导致近亲繁殖,进而种群衰退,公象成年后通常会离开象群,寻找其他象群中的母象,这是进化形成的避免近亲繁殖的机制。
群中的成年母象需要跟群外独立活动的成年公象交配繁殖后代。如果群象与其他象群长期隔离,缺乏基因交流,种群就难以为继。
“总有一天,我们要去想办法跟身边的野生动物共处”
全现在:在劝返大象、避免人象冲突方面,国外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黄泓翔:我觉得这从根本来说,是如何减少人象冲突的问题。人象冲突是一个在全世界常见的现象,只要大象比较多的地方都存在。当大象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就有可能伤害农作物、财产,甚至人的性命。而冲突的反面就是当地人会对大象产生敌意,甚至采取一些伤害大象的行为。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比较严格,避免了这样的现象,但在国际上,相互伤害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
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尽可能减少大象接近人生活的地方。在非洲,人们会在大象去的农田周围安装蜂箱,因为他们发现大象会害怕蜜蜂,这样可以减少大象进入农田的频率。在人类生活区域周边,设立有辣椒水喷雾的围栏,也可以阻止讨厌刺激性气味的大象。
这些措施也都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蜂箱的维护和辣椒水喷雾的延续性。另外,设立比较结实的水泥桩围栏或者电网围栏,成本往往非常高。
至于大家所说的将大象麻醉之后运回去,操作上会有很多困难,尤其是面对一个象群,很可能会刺激到大象而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而且麻醉到运输的成本也非常高。在非洲的一些保护区,会涉及麻醉一些小象做小规模的运输,但我还没听说过麻醉一群大象的可能性。
实际上,短期里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对大象破坏造成的损失给予保险赔偿,或者帮助当地销售农产品、手工艺品、发展旅游业,来弥补损失。从宏观上来说,就要改善大象的栖息地,这是缓解人象冲突的根本办法,也是最困难的。
孙全辉:在印度,当地管理部门建立了一些大象迁徙通道,也建立了公众预警系统,一旦有大象进入村庄,会通过手机及时将预警信息发送给民众。这样的做法经过很多年之后,印度大象伤人的数量是在下降的。
在非洲,比如在波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数十个非洲国家,人象冲突也是常见问题。面对冲突,肯尼亚就从野生动物肇事补偿转变成一种奖励和激励的方式,鼓励当地居民主动监测大象的活动,来控制它们进入到农作物种植区。当地的一些保护机构,也会雇佣当地居民来专门监测大象的迁徙。最重要就是,他们会重新对土地进行规划,保证大象有充分的栖息空间,同时尽量避免种植大象喜欢吃的农作物。在尽量减少冲突的同时,当地也充分开展野生动物旅游,让当地社区居民能够从中受益,让人们意识到保护大象,不仅有利于野生动物,实际上也会提高自己收入。这样,他们更愿意参与到保护当中,而不是跟大象形成对立面。
全现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野象群北上事件?
孙全辉: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次大象出走,是一次全民教育的机会,能让大家了解到大象目前的生存状况,甚至关注更深层次的保护问题。亚洲象从全球来看,都是濒危物种,如果经历这件事之后,能有更好的保护措施和政策调整,倒是一次把危机变成机遇的事件。
黄泓翔:这件事情上,当人类觉得我们可以去改造自然,或者想去引导野生动物的行为,最后可能都会遇到很多挫败。我们更该做的事情,可能是应该想办法让大自然保持它原有的样子,让我们的行为能够更符合大自然的规律,而不是让大自然、让动物去遵从人类的意志。
如果这件事情在现场采取了各种措施都不够有效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人与野生动物越来越密切的交集一定是越来越多,其实无论美国也好,香港也好,很多地方都会在城市发现野生动物,总有一天,我们要去想办法跟身边的野生动物共处。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件事也会给带来启发——我们是否应该开始去想如何调整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习惯,更好的去适应一个与野生动物共存的世界。